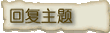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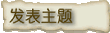 |
|
2023-06-11, 23:19
Post
#1
|
|||
|
主物质者
Group: Builder Posts: 19 Joined: 2023-01-15 Member No.: 102085 |
“The Inability of the Human Mind”: Lovecraft, Zunshine, and Theory of Mind Dylan Henderson “人类思维的无能”:洛夫克拉夫特、赞善与思维理论 翻译:利堪 校对:树源 熟悉H·P·洛夫克拉夫特的生活与作品的读者,在阅读丽萨·赞善(Lisa Zunshine)的《我们何以阅读虚构作品:思维理论与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时一定会对洛夫克拉夫特展开一次思考,因为无论篇幅长短,他的小说都使赞善围绕阅读的论断变得更加复杂。在《我们何以阅读虚构作品》中,赞善声称读者喜欢阅读小说,是因为这种文体戏谑地挑战了他们的“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挑战了他们解释看似模棱两可的行为举止,还挑战了这一过程中预测他人所思所想的能力:“我可以说,我自己阅读虚构作品,是因为它们能让我的思维理论变得精进。而且,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读过我的研究……我怀疑这也就是你阅读虚构作品的理由”(160)。 根据赞善的说法,小说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就像一团乱麻,必须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地解开。如此,以一种让读者感到既刺激又满意的方式,“参与、揶揄,并将我们的读心术推至极限”(4)。小说允许读者“尝试感悟不同的精神状态”,用“密切接触我们社会他者的思想、意图以及感受的权利”(25)诱惑他们。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赞善指出自闭症患者的经历,他们经常表现出“对虚构作品和故事讲述缺乏兴趣”(8),赞善声称,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理论受损,认为虚构作品描绘的复杂模糊的社会环境要么令人困惑,要么毫无意义。不过,尽管赞善的观点极其有趣,但也给熟悉H·P·洛夫克拉夫特生活与作品的人留下了一些未能回答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展现出受损的思维理论,却在虚构创作中极力压抑受损状态的作家来说,思维理论会如何解释这位作家的受欢迎程度呢? 当然,对洛夫克拉夫特这位已经逝世八十余年的人来说,追溯性诊断出他患有自闭症是不道德的,但即便是对他行为大概做一番分析也会发现,至少他的思维理论和他判断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是有限的。孩提时期,他就表现出了赞善论断中的自闭症儿童的“关键症候”,包括“社会和交流发展的严重受损,以及‘缺乏一般人的灵活性、想象力和假扮身份’”(8)。洛夫克拉夫特一贯性情严肃,对儿童游戏缺乏兴趣,他将自己的童年献给了认知追求:阅读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研究化学与天文学,创作故事、诗歌和散文。和他同龄的孩子令他“难以理解”: 你会发现我从未提过儿时友伴——我根本没有!我认识的小孩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习惯了大人的陪伴与交谈,尽管我在长辈身边感觉十分无聊,但我和那些黄毛小儿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嬉戏打闹令我难以理解。(Letters to Rheinhart Kleiner 35) 换句话说,洛夫克拉夫特发现同龄人的活动既缺乏吸引力,还令人费解。反过来,他的同龄人可能会觉得他既笨拙又奇怪。例如,克拉克·赫斯,是洛夫克拉夫特年少时期的邻居,她描述说有天晚上,当洛夫克拉夫特透过望远镜凝视时,邻居的几个孩子“聚集在远处看他”(Joshi and Schultz 166)。赫斯当时以为他很孤独,但当她接近他,鼓励他谈谈爱好时,洛夫克拉夫特没有读出她的主动背后是邀请他参与邻居间的交流,却解读为天文学探讨,还为她做出了专业解答,这迫使赫斯回到了朋友的身边。尽管此次交流极其简短,但强化了我们对年轻洛夫克拉夫特的看法——非常早熟,社交能力有限、似乎无法理解其他孩子相互交流的方式。 当然,赫斯和洛夫克拉夫特两人的形象都可能有所夸张——但事实肯定大差不差。在学校,洛夫克拉夫特有几个“儿时友伴”,包括门罗兄弟俩;一群男孩组成的“成员从九到十四岁不等”,他们一起组建了普罗维登斯侦探社(Letters to Alfred Galpin 19);还有哈罗德·W·芒罗(Harold W. Munro),此人写了一本简短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们在希望街高中共度的时光。即便如此,从这些不同的描述中浮现出的图景,是一个天赋异禀但举止笨拙的小孩,这个男孩,没有也无法轻易交友,只要与那些欣赏他强而有趣的才智的人相伴,他仍然富于魅力和创造力,甚至显得风趣。 随着洛夫克拉夫特年岁渐长,从青少年慢慢过渡到成年人,他依旧难以理解他人,准确衡量他们的所思所想。更重要的是,他压根没有这么想过。的确他在高中时恢复了某种社交活动,找到了意气相投的同伴,但他未能获取文凭,退居到一个僻静的内心世界达数年之久。例如,他与芒罗的友谊已经结束:“希望街的时光过后,我再也没有与洛夫克拉夫特说过话,但见过他几次。他非常内向,像侦探一样四处奔忙,弯腰驼背,胳膊下总是夹着书或纸张,目视前方,却谁也认不出”(Joshi and Schultz 163)。那时,芒罗肯定为自己昔日好友突然避世感到困惑,然而,洛夫克拉夫特似乎压根没有注意过芒罗;因为洛夫克拉夫特不仅没有在这些场合下与他交流,甚至认不出他。 不过,从洛夫克拉夫特参与业余新闻运动时的热情、后来他在生活中结交的众多朋友来看,他既不害羞也不厌世。如果说他苦于社交——在他前往斯莱特大道之前,以及离开希望街之后,显然如此——那是因为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即便是在与自己的妻子——洛夫克拉夫特拒绝承认其犹太血统,坚称她现在是“安格尔街598号的H·P·洛夫克拉夫特夫人”(Joshi and Schultz 126;italics in original)——互动时,洛夫克拉夫特似乎也无法判断其他人会对他的话作何反应。孩提时期,他无法理解其他孩子行为的原因,他长大后,也无法理解其他成年人。 1921年,30岁的洛夫克拉夫特写下了他最常被引用的结论之一:“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只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纪里,存在于那些依旧是人的人之中的怪客”(CF 1.272)。同样身为怪客的愁绪亘古不去,几乎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出现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每一篇故事里,从《印斯茅斯的阴霾》(“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旅行者发现自己深陷困境,孤身一人处于半人类怪物居住的城镇,到《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一位上了年纪的隐士发现与世隔绝的居所被外星人包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信件中找到更多这种无力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例子。事实上,这构成了他生活的一个主题,反复出现,例如,1913年他在《阿尔戈斯》(Argosy)中发起了一场令人惊讶又毫无必要的论辩,还有与同为作家的朋友罗伯特·E·霍华德(Robert E. Howard)时常紧张的关系中,都有所再现。有了如此之多的证据,加里和詹妮弗·迈尔斯在他们的著作《洛夫克拉夫特的综合症候》(Lovecraft’s Syndrome)中提出,尽管并不规范,但对这位已逝之人进行诊断是可行的。 洛夫克拉夫特受损的思维理论,在成年后转变为对普通人的内心生活彻底丧失兴趣,催生出了一部据赞善所言毫无存在理由的小说,因为它会尽一切可能挫败而非刺激读者的思维理论。洛夫克拉夫特篇幅最长的虚构作品《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连一个刺激读者思维理论、或是“将我们的读心术推至极限”的场景都没有。不像当代作家那样被教导去“陈列,但不要讲述”,洛夫克拉夫特避免摹仿(mimesis),偏爱叙事(diegesis),他把动作和对话描绘得如同实时发生一般。因此,《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几乎完全是由一系列的摘要组成的,对白尤为罕见。当角色互动时,洛夫克拉夫特会从远处描述,可以说,他的镜头从未拉近到足以观察身体语言或是面部表情等细微之处。 例如,考察接下来马里努斯·比克内尔·威利特医生与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医生告知老瓦德,尽管当局相信他的儿子已经逃跑,但实际上威利特已经杀死了那个冒充他儿子的人:“在发现瓦德失踪之后,医院方面立刻通过电话告知了他的父亲,但老人的反应似乎更多地是感到悲伤而非惊讶。而当韦特医生亲自拜访威利特医生的时候,威利特医生与他交谈了一段时间,同时坚持称自己并不知道瓦德在计划逃离医院,更没有与他有过串通”(CF 2.217)。请注意洛夫克拉夫特如何概括实际发生的对话——威利特和瓦德父亲之间的交流极尽简洁之所能,将原本可能是一章节的篇幅的讨论压缩成短短一个句子,剥夺了读者参与他的思维理论的任何机会。洛夫克拉夫特甚至仅仅用了寥寥数个字词(“更多地是感到悲伤而非惊讶”)(“more saddened than surprised”),便解释了笔下人物的情绪反应,进一步在过程中简化了互动。 洛夫克拉夫特概括意义重大的交流过程,随后告知读者其中涉及的情绪与动机,这一模式在整部小说中反复出现。大多数作家会用一整章来描写的关键场景被压缩成了几句话。例如,威利特尚未知晓瓦德已遭谋杀并被约瑟夫·柯温取代时,当他访问那冒名顶替者时,洛夫克拉夫特概括了整个交流过程,他拒绝给予人物为自己说话的机会: 然而,查尔斯并不会长时间的回应这种形式的问答测试。他非常概括地将与当下和个人有关的话题拨到了一边,而在面对那些和古老事物有关的谈话时,他也很快地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厌倦神情。他的目的非常明显——他希望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访客感到满意,并且就此离开,不再打算回来。(CF 2.313) 尽管这一场景被压缩过,但它不仅包含了对话的主旨大意——柯温(此处其身份被视作“瓦德”)拒绝探讨“与当下和个人有关的话题”,还解释了情绪(“厌倦”)(“boredom”)与动机(希望其“就此离开”)(a wish “to make him depart”)。 然而,引用的对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但洛夫克拉夫特利用对话不是为了调度读者的思维理论,而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结果就是,对话主要以旁白和信件的形式存在。例如,在小说的结尾,洛夫克拉夫特引用了威利特的话,他说:“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但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有许多种魔法。我做了一个大净化仪式,这对那些睡在这座房子里的人更好一些。”(CF 2.359)然而,没有任何交流。读者永远无法知道瓦德的父亲如何回应这段意义重大的述说,也不会了解与叙述者或环境相关的更多信息。他们的对话发生在真空之中,没有告诉读者任何涉及人物的信息。的确,极少的对话往往会给读者一种错误的人物印象,也就是说,洛夫克拉夫特肯定无意传达出这种印象。例如,许多读者,包括笔者本人,都会从威利特自夸式的声明推断出,他,用学者S·T·乔西(S. T. Joshi)的话来说,“嚣张跋扈又妄尊自大”(IAP 669),在此过程中,想象出的英雄形象与洛夫克拉夫特意图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 对洛夫克拉夫特而言,对话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强调特定观点的方法。至于人物以及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都不重要。人物存在是因为情节需要,但是就复杂性而言,他们在成人文学中是最简单的。例如,柯温邪恶,瓦德显得幼稚,他的父母满怀慈爱。就像洛夫克拉夫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苦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他觉得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了无生趣。“关键的是我对日常生活缺乏兴趣,从来没有人写过没有真正情感驱动的故事——可我呢,恰不具备那种驱力[……]人类个体和他们在自然法则中的命运于我影响甚小”(SL 5.18–19)。通过将信件混入文本,洛夫克拉夫特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因为它们让他绕开可能暴露人物脆弱之处的互动。例如,当威利特决心必须杀死仍被瓦德父亲视作儿子的柯温时,他给老瓦德写了一封信,到洛夫克拉夫特完整引用了出来。这封信告知瓦德父亲他将再也见不到自己儿子了,洛夫克拉夫特将原本一个充满情感的场景,一个需要复杂人物和互动、能够挑战读者思维理论的场景,改造成了几个简单的段落。洛夫克拉夫特甚至解释了老瓦德的反应,陈述道那位“有些晕眩的父亲”发现“在看过医生寄来的信后,他仿佛找到了某些能够让自己镇定平静下来的东西——可在其他人看来,这封信似乎预示着绝望,而且似乎还导出了全新的谜团”(CF 2.361)。 然而,洛夫克拉夫特的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确实比《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包含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塑造。诚如斯言,洛夫克拉夫特时常会展示出一种刻画令人难以忘记的人物肖像的非凡能力。其中之一,读者想起《墙中之鼠》(“The Rats in the Walls”)中的德拉波尔(Delapore),一个“因伤残而退役”(CF 1.377)并在儿子死前照顾儿子的人;或是《印斯茅斯的阴霾》(“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中的罗伯特·奥姆斯特德(Robert Olmstead),学会了沉湎于他一度与之抗争过的可怕转化;抑或是《超越时间之影》(“The Shadow out of Time”)中的纳撒尼尔·温盖特·匹斯里(Nathaniel Wingate Peaslee),被除了小儿子以外的所有人抛弃。不过,请注意洛夫克拉夫特塑造这些人物的手法。他既没有为读者呈现多个人物相互互动的冗长场景,也没有奉上谜语——换句话说,孜孜不倦的读者必须细致分析才能真正理解每个人物的内在本质,洛夫克拉夫特采用了一种开门见山、无需任何思维理论的的途径。他以描述性语句的形式,只用几道快速的笔触,就为自己的创作增添了背景与深意。例如,在《印斯茅斯的阴霾》中,洛夫克拉夫特仅用一段话,就概括了奥姆斯特德对自己杂种血缘的日益接受: 眼下,我还没有走到道格拉斯舅舅那一步。我随身带着一把自动手枪,几乎要迈出那一步去。但某些梦境阻止了我。极度的恐惧 正在逐渐减退,我奇怪地觉得自己正在被牵引向未知的海底,却不再为它感到恐惧。我在睡梦中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做出奇怪的事情,接着在欣慰而非恐惧中醒来。我相信我不需要像是大多数人那样要等到完全转变的时候。如果我等到那一步,父亲或许会像舅舅对待可怜的表弟一样,将我关进一家疗养院。前所未闻的伟大荣光正在海底等待着我,而我很快就能去寻找它们了。呀-拉莱耶!克苏鲁-富坦!呀!呀!不,我不能自杀——我不可能注定要自杀!(CF 3.230) 洛夫克拉夫特并未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思维理论来想象奥姆斯特德的所思所想,而是就此告知自己的读者他们需要知悉的一切。的确,这一段话涵盖了奥姆斯特德整个转化过程:从他考虑向自己开枪开始,止于坚定认为“不可能注定”要射杀自己。读过赞善的论点后,人们可能会认为读者被洛夫克拉夫特直白方式欺骗了,但诗歌般字字珠玑的文本,让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并没有显得平淡或直截了当。 如果洛夫克拉夫特尽可能消除读者参与思维理论的机会,那他的虚构作品又为何如此受人欢迎呢?也许有人会说,洛夫克拉夫特主要写的是短篇故事,并不需要像中长篇小说中那么多对读者思维理论的挑战。不过,《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是一部51500余单词的中篇小说,而根据“H· P·洛夫克拉夫特档案馆”(H. P. Lovecraft Archive)组织的一场在线调查,除了另外三篇故事外(“访问者最喜欢的故事”)(“Visitors’ Favorite Stories”),网站访问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最高。虽然赞善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但也许洛夫克拉夫特通过淡化思维理论,让作品对某些读者更具吸引力。例如,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他欣赏并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他就认为怪奇小说对超自然的关注是一种财富,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受欢迎的变革。当其导师乔治·斯特林(George Sterling)敦促他抛弃宇宙空间,转向关注世俗时,史密斯谴责了赞善所称道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作品歇斯底里、鼠目寸光:“我[……]拒绝屈从于时下贫瘠荒芜、庸碌世俗的精神;我坚信迟早会兴起一场浪漫主义复兴——一场对机械化和过度社会化等等问题的反抗[……]普罗大众的道德准则或审美意趣,对我而言毫无吸引力”(264)。 洛夫克拉夫特本人对此也深有同感。在其论文《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中,他批评雪利登·拉·芬努(Sheridan Le Fanu)、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罗伯特·露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以及其他十九世纪恐怖作品创作者过分专注于“事件”而“忽略了气氛细节”,对恐怖小说,这些细节重要得多:“[这一作家流派]因其‘人性元素’而比真正的艺术性恐怖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不过咎其为何无法企及后者之高度,也只因稀释过后的作品的强度完全无法与浓缩之精化相提并论”(48)。赞善从不承认某些读者会觉得她所欣赏的丰富细致的人物刻画会令人厌倦,属于一种分散故事本身注意力的过分干扰。事实上,也许更多的读者会站在洛夫克拉夫特这边,而非赞善,赞善推崇的作家,尤其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这样的作家,许多读者——并非全部患有自闭症——认为他们要么令人乏味,要么令人困惑。我猜测,更多人会赞同洛夫克拉夫特对亨利·詹姆斯的评价,他称这位作家“太过散漫,而用词也多油滑世故,并过于纠结字面上的委婉,因此无法将其故事中天马行空的强大恐怖发挥至极致”(Annotated Supernatural Horror 68),却不会认可赞善。 淡化思维理论的好处并非微不足道。通过这种做法,洛夫克拉夫特吸引了那些像史密斯一样,寻求想象逃避时而压抑的人文主义的人。洛夫克拉夫特偏爱叙事胜过摹仿,这是他贬抑思维理论的方式之一,也塑造了他的写作风格,以至于让他的文章变得驳杂繁琐。如上所述,在《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中,洛夫克拉夫特经常将可能写得冗长的场景压缩成几句简短的句子。这种做法使他可以大大加快写作速度。结果就是,他的许多作品都显得远比实际上更长。就像《畏避之屋》(“The Shunned House”)这篇以10700余单词事无巨细地重现了一座有两百年历史的鬼屋的故事,看来更像中长篇小说或历史教科书,而非短篇故事。不过,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情节和那些更长的小说一样复杂,但即便是像《疯狂山脉》和《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这样最长的作品,也遵循着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效果统一论(Unity of Effect)。如果洛夫克拉夫特像大多数其他当代作家那样,把场景描绘成就好像它们是实时发生的一样,那么他作品里所达成的专注和干净将会荡然无存。特别是对话,这会破坏洛夫克拉夫特认为对成功的怪奇故事至关重要的气氛,而二十世纪的语言模式会对于他独特、刻意做旧的长篇大论造成浩劫。当然,洛夫克拉夫特确实会写一些对话。例如,《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以威利特与柯温之间的对话作结,这是整部中篇小说里唯一一场有来有回的交流。它因其稀有性而更具力量感。 正如赞善著作的标题所暗示的,她的《我们何以阅读虚构作品》立足于一个假设:我们确实会阅读虚构作品。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也许她推崇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亨利·詹姆斯所代表的方法是部分原因。洛夫克拉夫特对赞善所欣赏的风格做出了反应,他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作虚构作品,有意淡化人物、他们的内在状态、以及他们的互动,而他作品长期以来广受欢迎,似乎不仅挑战、更是瓦解了赞善的命题。最简单的解释也许是,如果将大多数读者置于一个谱系之上,他们与自闭症患者的共同之处会多于文学评论家。不论如何,许多读者,包括笔者本人,会赞同洛夫克拉夫特的观点——“生活使我想要逃离生活”(Letters to J. Vernon Shea . . . 30)。 原文引用: Joshi, S. T. I Am Provide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H. P. Lovecraft.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10. 2 vols. Joshi, S. T., and David E. Schultz, ed. Ave atque Vale: Reminiscences of H. P. Lovecraft. West Warwick, RI: Necronomicon Press, 2018. Lovecraft, H. P. The Annotated 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 Ed. S. T. Joshi.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rev. ed. 2012. ———. Letters to Alfred Galpin. Ed. S. T. Joshi and David E. Schultz.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03. ———. Letters to J. Vernon Shea, Carl F. Strauch, and Lee McBride White. Ed. S. T. Joshi and David E. Schultz.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16. ———. Letters to Rheinhart Kleiner. Ed. S. T. Joshi and David E. Schultz.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05. Myers, Gary, and Jennifer McIlwee Myers. Lovecraft’s Syndrome: An Asperger’s Appraisal of the Writer’s Lif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2015. Smith, Clark Ashton, and George Sterling. The Shadow of the Unattained: The Letters of George Sterling and Clark Ashton Smith. Ed. David E. Schultz and S. T. Joshi. New York: Hippocampus Press, 2005. “Visitors’ Favorite Stories.” The H. P. Lovecraft Archive, 27 October 2011,hplovecraft.com/writings/favorites.aspx. Accessed 26 October 2018. Zunshine, Lisa.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简要说明: H.P.洛夫克拉夫特及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以指数级增长,因为两家主流媒体的投机活动即将发布。导演科幻电影《霹雳战士龙》(Hardware)(1990)而广为人知的邪典导演理查德·斯坦利(Richard Stanley),刚刚完成了由尼古拉斯·凯奇(Nicholas Cage)主演的电影版《星之彩》(“The Colour out of Space”)的导演工作(遗憾的是,斯坦利在其电影片名中使用了“颜色”一词的美式拼写)。剧本是由斯嘉丽·阿玛里斯(Scarlett Amaris)所撰写。凭借恐怖电影《逃出绝命镇》(Get Out)(2017)而声名鹊起的非裔美国人导演乔丹·皮尔(Jordan Peele),已经完成了对马特·拉夫(Matt Ruff)的小说《恶魔之地》(Lovecraft Country)(2016)的改编,使之成为HBO电视台的八集迷你剧。规模要小得多的,是S. T.乔希参与了五部即将上映的关于洛夫克拉夫特的纪录片的制作:两部法语片(由吉尔斯·梅内加尔多(Gilles Menegaldo)和马丁奇·弗洛特(Martine Chifflot)导演),一部在加拿大上映(由卡伊斯帕沙(Qais Pasha)导演),一部是一档日本电视节目(《暗界之秘》(Dark Side Mystery),在NKH公共电视频道上映),还有一部是一档法国电视节目(上映于欧洲文化电视频道ARTE)。此外,卡达布拉唱片公司(Cadabra Records)刚刚以密纹唱片形式发布了乔西的《<洛夫克拉夫特:短篇传记>选集》(Selections from“H. P. Lovecraft: A Short Biography”)。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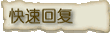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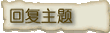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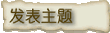 |
| Copyright © 2005-2024 The Ring of Wonder | Time is now: 2024-06-04, 17:18 |
 161
161 17
17